在中国当代文学中,余华的《活着》无疑是一部极具震撼力的作品。它以冷静克制的笔调,讲述了一个普通农民福贵在动荡历史中的一生。他经历了家道中落、战争、饥荒、政治运动,并接连失去所有亲人,最终只剩下一头老牛相伴。然而,正是在这种近乎残酷的苦难叙事中,余华向我们揭示了生命最本质的命题:活着本身,就是一种尊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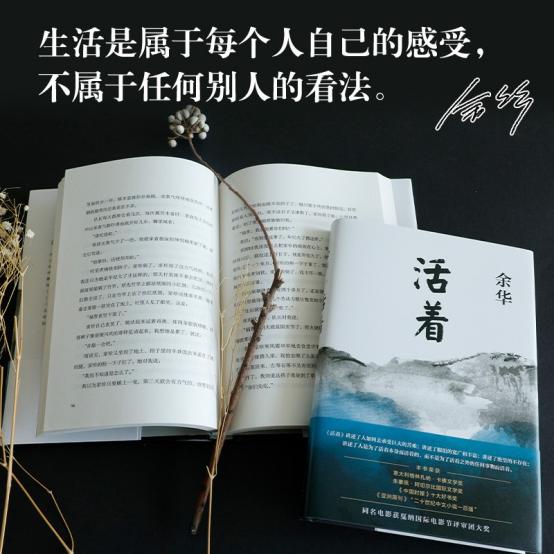
一、历史的碾压与个体的渺小
福贵的一生,几乎贯穿了20世纪中国最动荡的几十年。他从地主少爷沦为贫农,历经内战、土改、大跃进、三年自然灾害、文革等一系列历史事件。然而,余华并未直接描写这些宏大历史,而是让它们成为福贵命运的暗流。比如,有庆的死源于大跃进时期的医疗资源匮乏,凤霞的难产暗示着农村医疗条件的落后,而家珍的软骨病则与长期的贫困和营养不良相关。历史像一台无情的碾子,而福贵这样的普通人,只是被裹挟其中的一粒尘埃。
这种叙事方式使得《活着》超越了单纯的家庭悲剧,成为一部关于个体在历史洪流中如何生存的寓言。福贵没有能力改变时代,他唯一能做的,就是在每一次打击后,继续活着。这种看似被动的生存状态,恰恰体现了生命最原始的力量——在不可抗拒的命运面前,坚持不倒下,就是一种抵抗。
二、死亡的重复与生命的韧性
《活着》最令人窒息的地方,在于死亡的频繁与无常。福贵的亲人一个接一个离去,每一次死亡都突如其来,毫无英雄主义的渲染:
父亲被他气死,从粪缸上摔下身亡;
母亲因病去世,他甚至没能见到最后一面;
儿子有庆被抽血过多而死,荒诞而残忍;
女儿凤霞产后大出血,刚获得幸福就突然离世;
妻子家珍在长期病痛中默默死去;
女婿二喜死于工地事故;
外孙苦根因吃豆子撑死……
这些死亡没有逻辑,没有救赎,甚至没有解释。余华以近乎冷漠的笔调叙述,使得死亡不再是戏剧化的悲剧,而是生活中无法逃避的常态。然而,正是在这种死亡的重复中,福贵的生命力显得愈发顽强。每一次失去,他都痛不欲生,但每一次,他都会重新站起来,继续活着。这种近乎固执的生存意志,构成了小说最震撼人心的力量。
三、活着的意义:从“为什么”到“就这样”
在传统叙事中,苦难往往被赋予某种意义——或是道德的考验,或是成长的契机,或是命运的馈赠。但在《活着》中,苦难毫无意义。福贵没有因为苦难变得更高尚,也没有因此获得任何超越性的领悟。他的活着,既不是等待救赎,也不是追求幸福,而仅仅是一种本能的坚持。
这种对“活着”的诠释,与加缪的《西西弗神话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西西弗被诸神惩罚,永远推石上山,石头滚落,他又重新开始。加缪认为,“我们必须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”,因为正是在这种无意义的重复中,他战胜了命运。福贵也是如此,他的活着,不是出于某种崇高的理由,而仅仅是因为“人活着,就是这样”。
在小说的结尾,福贵买下一头老牛,给它也取名“福贵”,并对着牛自言自语,仿佛在向它讲述自己的一生。这个场景极具象征意义——当所有亲人都已离去,记忆成为唯一的陪伴;当无人倾听,讲述本身就成了活着的证明。福贵的活着,不再是为了任何人,甚至不再是为了自己,而仅仅是因为生命本身还未终结。这种剥离了所有附加意义的生存状态,恰恰揭示了生命最本质的样貌。
四、结语:活着的尊严
《活着》之所以能跨越时代与国界,打动无数读者,正是因为它触及了人类最根本的生存命题:当一切都被剥夺,生命还剩下什么? 余华的答案是:即使一无所有,活着本身,就是一种尊严。
在当今社会,我们习惯于赋予生命各种意义——成功、爱情、家庭、理想……但《活着》提醒我们,生命的价值并不完全依赖于这些外在的东西。福贵的一生没有辉煌的成就,没有幸福的结局,甚至没有精神上的顿悟,但他依然活着,依然在清晨牵着老牛走向田地,依然在黄昏时对着天空喃喃自语。这种最低限度的生存,恰恰是对命运最有力的回应。
余华用福贵的故事告诉我们:活着,不需要理由;活着,本身就是理由。
推荐人:徐贤凤
审 核:黎意慧
编 辑:李翰帆